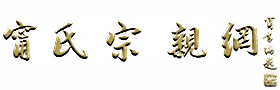|
甯肯访谈录
http://www.ningcn.com 2003/7/13
我的小学中学是在“文革”期间度过的,67年-77年,一点没糟踏。我所在的小学叫北京琉璃厂小学,现在是文化街了,那时就一个荣宝斋,我上学时已改卖毛主席像了。
我们家住在琉璃厂一个胡同里。我应该是66年上小学,但“文革”一开始就乱套。那年没招生,毛主席说,不招了再玩一年吧,就不招了。我想他是这么说的,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,除了他还有谁敢让全国的孩子说再玩一年就再玩一年。
我八岁多上学,说老实话还不想上呢。我成长于文革十年,文革实际与我们这些孩子没太多关系,如果说有,那就是我们大体处在一种野生状态中。在破碎中疯长,毫无规矩,没大没小,与老师平起平坐,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,特“后现代”。
我在《我的二十世纪》里对此有一些描述,这里不多说了,只想说一点,“文革”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,绝不是一个简单罪恶的符号,其对中国人深层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,我们对此开展的研究像关于其罪恶部分的研究一样,少而又少。
我可以说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旅行吗?我并非完全在另一种意义上讲话。
我五六岁之前每周都要坐火车跟着父母往来于北京与良乡之间,他们在良乡工作,我差点就生在良乡。
每个周末他们带我乘火车回北京,与哥哥姐姐团聚,我从襁褓到六岁都是这样。我觉得五六岁以前的记忆跟子宫里的记忆没什么区别,一片蒙昧,混沌不清。我多少能找回的是那时的一些心情和模糊的图景,比如早起赶火车,天不亮就走,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的街灯,那种十字街头的街灯,暗红,清冷,街上阆无人迹,我心里说不出觉的难过。
我还依稀记得在火车上,过一些桥和大河,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害怕,好像火车随时会开进河里,过了河我才觉得安全了。我注视窗外,田野不必说了,我看到一些房屋,坟头,巨大的石碑。石碑给我的印象像危险的河流一样深,是抹不掉的神秘记忆之一。
很久很久以后,我在母亲的病榻上才知道,那河是永定河,那桥是芦沟桥,那碑是桥边的老王八驮石碑。小时候我曾多少次穿越芦沟桥,我都不知道。
六岁以后我停止了这种跟随父母的漂泊,过上安定生活。直到十六年以后我才再次坐上火车,离开北京,开始一次自觉的旅行。
那是1982年,我大学三年级,与同学结伴去了济南,青岛,大连,不仅坐火车,还坐了船。在火车上,我记得我跟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,我完全忘记小时的事了,对坐火车的感觉十分新奇。
后来我去过的地方主要是西藏,长达两年。三峡,秦岭,海南,甯夏,深圳,俄国远东城市与河流,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给我留下了不同的心情和印象。
但都与西藏无法比拟。
我在作品中已经写了一些旅途中难忘的些事,有件事还没写,我觉得在这里值得一提。
我前面提到的第一次旅行,在济南,去洛河镇看黄河。黄河如雷贯耳,可第一次见到黄河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,如此窄的一条河,看上去也就五六百米。
我下了河,走出去很远河水才到我的膝盖,我决定渡过去。我顺流而下,过了黄河大铁桥多一半的桥孔,水很急,但一伸脚仍能够到底。我仰面漂在河上,根本不着急渡过去,捉摸着一首诗的写作,完全忘了黄河的凶险。后来我快近对岸了才越来越感到黄河的力量,流速快得像墙壁一样,眼看对岸不远了,却总也到不了。非但如此,似乎反而开始离岸越来越远,我侧头一看,远处矗立着白花花的高墙,像夏日阳光下明晃晃的露天体育场看台,而我所要抵达对的岸此刻远离了我,直线已变成的弧状,我奋力游,弧度竟越来越来渺茫,再看那高墙我突然明白,并暗吃一惊,原来我这是到了黄河大拐弯的地方,黄河已变得十分开阔,那高墙原是黄河转弯的大堤!我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苍茫黄水,一个人在河上,一下慌了,不知如何是好。
想想开始时我还躺在黄河上写诗呢,现在突然感到直逼死亡。我顺流向大堤游,我看到黄河在转弯处形成的巨大漩流,我被裹携,别无选择,逆流向堤上冲。过了不知多久,我渐渐接近堤岸,希望已在眼前,可浊浪也越来越急,我几次手都摸到了岸又被冲走了,那种打击惊心动魄!最后当我拼命抓住岸边一块石头,撑起来,扑到岸上,向上看了一眼就闭上不动了。
不是因为累晕了,是我在哭泣,亲吻石头,大地。我四点多下水,现在夕阳已落下地平线,在水中我挣扎近四个多小时。我沿着生满野蒿的黄河滩走,小跑,我知道同伴们得等得我多着急,天黑下来,还有一点点亮度,我看到来寻找我的人影,你可以想象我们见面的情景。
当我回忆这件事,我觉得像是又经历了一次这件事。
我觉得自由是可以涵盖一切的概念,是生命的本质属性。我理解的自由就是让生命达到最大的熵。惯于压抑自己的人,常常是压抑别人的高手,酷爱自由的人也一定愿还别人更多自由。我不愿谈论死亡,讨厌死亡,我觉得我与死亡势不两立。
爱情和太多东西相关,但有时又似乎是毫无关系。仅从男女之间的差异,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人悲观。比如男人倾向于简单的爱情,而女人绝对反对简单化。在短暂的爱情里,这种相对小一点,甚至没有,但只要一长这种基本矛盾就会暴露无遗,我认为永远无法得到解决,除非将来人类有一天都变成以双性人。
我已经写作的时候,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作,甚至当我已写出了一篇四千多字小说的时候,我仍不知道自己是在写作。
1977年我上高二的时候,那时没高三,高二就到头了,下半学期重新分班,把好学生与差学生分开重组,所谓的快班慢班。我们班被拆了,我的好多哥们被分到别的班。我虽然学习差,但地位特殊,是班军体委员,纪律方面得靠我镇着,而且我量他们也不敢分我差班去。
但别人分到了差班,我觉得一种巨大的侮辱,感到悲愤。
那时我刚读完苏联一本叫《人世间》的小说,那里有着一种无法言状的悲愤在里面,正好语文老师作文题目下来,叫“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”,我不管那套就按自己的方式写起来,大致情节是一个叫王奇的学生被分到了慢班,心里悲愤交加,回想自己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,现在正要发奋图强却被分到慢班,开始自暴自弃,与他前班主任尖锐地对立,做出一些事情,后来他留在快班的哥们找他,帮助他,最终使王奇思想转变,发奋图强,学习成绩直线上升,后来又回到快班。
作文居然写400字稿纸十二页,抄袭了《人世间》中养蜂人、退休将军悲愤时的心情,诸如“出神地望着天花板”“万念俱灰”之类。
作文交上去了,结果语文老师用了一节课讲我这篇作文,又拿到别的班去讲,全年级震动。一些其他班老师好奇地问我有没有“模特”,我当时听愣了,不知什么叫“模特”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虚构,完全按想象中的真事写的,老师在讲我这篇作文时才给定性为小说。我的作文破天荒得了优,这以前我全都是中。
从那时我爱上写作,开始补习有关小说的基本常识。不久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发表了,我认真看了,颇不以为然,觉得不如我写得感人。从那时到现在,应该说我写了二十多年了,中间断了五六年,搞公司去了,但始终也没忘了有朝一日重新拿起笔。
要说写作对我的意义,倒不如说我常常感这样的反题:我对写作的意义。这或许过于自恋,但没有这种真实的自恋、自命不凡,我认为写作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能设想我写的东西是差的东西,我必须感觉那是非我莫属的东西。
这也是我写得少的原因之一。
城市与大自然应该交替出现在人的生活里,我们在城里向往大自然,事实上,我们在大自然时间长了会比向往大自然更加向往城市,是城市的出现才使自然界获得了另外的意义。城市使人的心情变得复杂,自然则使人归位,但我认为归位只能是一种体操,而不能变成一种常态,否则自然界将失去城市赋予它的意义。我因为热爱城市生活,所以才更加热爱大自然。
是山脉与河流。大海虽然辽阔,纯净,但一览无余,缺少可以把握的变化。山脉由于视觉上遮住了你,因此更加吸引你,使你想知道山后有什么。此外山给人一种鼓舞,一种向上的信念和坚定,这是我喜欢山的原因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水,我是说河流。
我总觉得河流与男人有一种亲缘的关系,它的动感,弯曲,裸露,空灵,缥缈,可以触摸,最接近于女性的美。所谓勾魂摄魄,我认为河流与女人不相上下。而“仁山智水”,我觉包含了女人的视角,女人最欣赏男人的是什么呢?仁也,智也。
上帝既然创造了我,肯定有他的想法,我想印证他的想法。
我的阅读杂乱无章,不成系统,不求甚解,不作笔记,记不住情节。以前是逮着什么书看什么书,现在是习惯先嗅一嗅开头,中间,是否是我喜欢的那种质地的语言,那种感觉,如果是,不管写的是什么,我会认真的像吸毒一样地读下去,我愿忘记作者,手法,决不有意识记一些东西,而是让它深入我的骨头和血液,永远奔流在我的血管中,最终它会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不清楚。
我不固定喜欢哪一个作家,常常我只是喜欢一个作家的一本书,甚至一篇文章。比如我喜欢萨特,但只喜欢读他的《答加缪书》,真是棒极了,这篇文章我读了有十五年了,有一阵子天天读,大声朗诵,十几年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。
看看萨特与加缪是怎样交锋的吧,高蹈,谦逊,锋利,尊重,讥讽,智慧,直言不讳。咱们呢,就是骂,对骂,什么呀都,乌泱乌泱的。真的,你真的不敢着他们,溅你一身,或爬你一身,你糟心不糟心呀。
到目前为止我只读了萨特的《答加缪书》,《厌恶》及其它我都没读完或读进去。我是一个很荷刻的人,对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挑挑捡捡。我犯不上把握一个作家的全貌,我只丰富我自己喜欢的气质,在阅读中发扬它们,锤炼它们。
让我读的入神的作品(小说)主要是这些:《唐璜》、《牛虻》、《九三年》、《城堡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局外人》、《喧哗与骚动》、《一个女士的画像》、《灰色马,灰色的骑手》、《百年孤独》。
我经历过不下五种职业,首先这五种职业综合起来对我构成影响,也符合我的性格特点,一种职业无疑是一种经历。
现在下岗失业不再新鲜,但1989年还是很新鲜的,我在那一年丢了饭碗,做起了推销员。各种职业中对我最没影响的是教师职业,我大学毕业当了中学教师,我天然不适合从事教师工作。当然事实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对我构成决定意义的影响,泥瓦匠与推销员时间都比较短暂,只是使我认识到社会不同方面,记者使我有机会到处跑,去想去的地方。但新闻这行我并不喜欢,我觉得新闻写作是一种无效劳动,太易碎了,不能有自己的个性,而且虚假,我厌恶新闻工作。
我还做了几年广告人,创办了广告公司,大体知道公司运作、老板是怎么一回事,对一些东西不再恐惧。综合起来说,职业的变迁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变得豁达,大度,无论失意得意,我始终没让我忘记写作,我最爱的还是写作,是写作使我无论怎么变,都万变不离其宗。
我想主要是我二十几岁在西藏的漂泊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,它使我的内心变得乐观,透彻,广阔,自信。很多事情我都不由得有一种超越的品质,直接的影响体现我的文字中。
目前我写的所有作品都与西藏有关。西藏可能比我读的书对我的影响还大,没有西藏的两年,我很可能会放弃写作。我曾在一些作品中描述过一次在街头听《阿姐鼓》的情形,那时我驾车在东单银街上,去天伦王朝饭店谈一笔广告生意,路上堵车,突然从街边音像店传出《阿姐鼓》的声音,我当时真是魂飞天外。
谈完生意,我立刻返回那家街边店,买了那盘CD,回家听了一两首歌,赶快关掉了。我不敢听下去,再听下去我什么也干不了,我满脑子西藏,仿佛自己是一只野鸽子在西藏的河流上飞。我竭力抑制着自己,把盘封存起来,我想等我退出公司再听吧。那时我要拿起笔一猛子扎下去,痛痛快快写。
1997年下半年我终于看到了退下来的希望,我把完整精力投入到写作上,边听阿姐鼓边写,阿姐鼓七首歌,我当时计划也写七篇散文,阿姐鼓给了我一种写作形式。我写完了《沉默的彼岸》初稿,正好去昆明开一个会,就去了《大家》编辑部,见到海男,令我惊奇的是海男拿起我的稿翻了两下,离鼻子很近,好像还闻闻了,就说行了。我说你还是看看再决定,海男说不用了,有些稿子随便看几行就知道行不行。海男嫌短了点,我说,七篇还短?海男说他们准备推出一个叫做“新散文”栏目,要求作品有相当长度,每次推出一个作者,让我回去再充实。
我放弃写作已经快五年了,这是我五年来第一篇作品,竟如此顺利。从此我又走上了写作之途。没有西藏的漂泊我还能回到写作上吗?
很难说,我当时应该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,车,手机,生意场,一切职务之便,包括国外考察,我都放弃了。没有西藏我能放弃吗?
我想写作是我内心最大的情结。我刚才说把一切都视为审美体验,审美体验是幸福和生命的最高准则,但体验之后是什么?我想就是写作。
写作使我人生有一条主线,将我的生活串连起来,并由此获得意义。写作使我能够做到对很多事情既入乎其中,又超脱其外,什么也不能真正将我击倒。写作使我宽以待人,因此有很多朋友,很多快乐。
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,把一切都视为生命的体验,在审美面前,没有是非,没有对错,没有成败,像所有人那样去爱恨、喜怒、争抢,然后超越。我认为达到这一步,你就永远是快乐、幸福的。 相关资料:
《蒙面之城》本站下载:
http://www.ningcn.com/download/meng.zip 作者宁肯介绍:
http://www.ningcn.com/list.asp?id=221 著名作家宁肯给本站的留言:
http://www.ningcn.com/list.asp?id=244
原作者:甯肯
来 源:
共有3709位读者阅读过此文
|